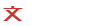思念故乡优美散文汇总3篇
月亮里有我们每个人所留念的故乡,不论你身在何处,飘零何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思念故乡优美散文,供大家欣赏。
思念故乡优美散文:故乡的水井
从远离故乡那天起,我再也不见过故乡的水井。可是,在我心中,故乡的水井,却一直牢牢地占据着我的空间,似乎水井变成了一首优美的抒情诗,使我爱不离嘴。现在,当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浮现出,故乡那口爬满绿苔的井口,想起许多童话般的故事。
想起故乡的水井,便想念起故乡的水伯。每当风雨过后,他都要拿着一把扫把来到井边,将水井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几十年如一日,故乡的水井始终保持着纯洁。目前,我尽管生活在大西北,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梦起故乡的水井与水伯,走路时也不断的想起他们,与朋友骑马在大草原上奔驰时,也曾经轻轻地唤过他们。是的,他们是我生命中的两个小世界,那么近,又那么远,永远没有休止地浮现、磕碰、漫游。在我的梦中,故乡的水井总是长着青苔,水伯总是弯着腰打扫。这一切,都是这样的原始。
九十年代初春,我从西大来到陕北一个小山村体验生活,又重新看到了水井。这一口干枯的水井,又把我带回到故乡的童年坐的水井,沉湎于深远的日子。
童年时代,我常常趁爸妈不在家的时候,自己提着一只小水桶,到水井边打水冲凉,可是,水伯一见到我自己打水,他就走过来和蔼地说:“孩子,别自己来水井打水,以免掉落入水井。”说着,他一边帮我打水一边帮我洗澡,犹如自己的父母对待孩子一样。然后,给我穿好衣服送我回家……在他老人家面前,我表示不再单独一人到水井边打水洗澡了。可是,过后我又偷偷地去洗澡,又被他抓住送回来,一次、二次、三次……我再也不单独到水井边洗澡玩耍了。
故乡的井水是清澈纯洁的。当你站在井湄,把水桶慢慢的往井底扔时,自己的影子倒映到水井底下面真有意思。这时,你如果乘着这一刹那间的空间里看自己的影子,比在镜子里显得更加真实、优美。因为,故乡的水井是原始的,而原始使我看到了最真实的自我,没有半点虚伪。扔下了水桶,用力拉住绳子左右一摆,水桶翻了,水就咕嘟咕嘟的满了,拉上台湄,你看着装满清澈见底的故乡水,心里就像蜜糖甜蜜蜜的。当然,有时井水也有浑浊的时候,那是雨后水流进去了,不过,这种原始的井水总比城里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纯洁得多。
六月份,是南方刮台风的旺季。一次,十六号台风把许多树枝、杂草都刮到水井里,水伯为了打扫干净,使乡亲们天亮时能喝上清净的井水,天蒙蒙亮就点上马油灯来到水井打扫收拾,像打扫自己家一样的细心。他连干了几个小时,天亮时,乡亲们挑着水桶来到水井挑水时,这位七十一岁的水伯却倒在水井栏旁,再也起不来……台风,夺走了水伯的生命,不,是水伯为了乡亲们的生命而贡献出自己的余生。
虽然,水伯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可是,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水伯朴实、无私的崇高形象与那清澈纯洁的故乡水井,心里就产生起一种敬佩、内疚、不安。如果我们都像水伯与井水一样纯洁清澈,那多好啊!
思念故乡优美散文:低头思故乡
老祖先什么时候因啥给我们村起了那么好个名字,实在是无从考究。在刘集地面甚至更大的范围,人们都知道胜光村包括赫、惠、赵三堡子。赵家堡子大一点,也不过三十来户;赫家堡子最小,包括后来移居村外的几户,总共有20户吧!说来也怪,三个堡子的姓纯之又纯。特别是惠家堡子,用当地人的话说,没个杂木楔楔。赵家堡子有几户李姓,却散居在北门外头;赫家堡子的几户惠姓,是惠家堡子的两支血系,一曰锡户,一曰经户。
我常常有种了却不了的心愿,写一写这古老的胜光村,写一写生我养我的惠家堡子。每每提起笔来却无从着手。故乡在炎黄子孙的历史上和心目中,哪怕是不值一提的,而在自己的心中无论如何是神圣的啊!唐大诗人李白面对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不就是种圣洁的感觉吗!我低头思故乡,以表示向故乡致敬!
家乡藏着我一辈子的记忆。
我是惠家堡子人,一辈子觉得惠家堡子的人最亲。小时候,不管是本家人还是旁系宗族,都亲亲地喊我旺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人都爱逗我玩。不知谁给我起了个叫“老瓮”的外号。直到如今我回家乡去,年纪长点的人还会高兴地夸耀说,老瓮回来了!这外号的来由是我小时候长得又胖又矮,像一条盛水的老瓮。叫着叫着咋都觉得亲呢。后来我发现这就是爱称,也是家乡人刻在我心中的记号,是我和家乡人的感情哇!
离开惠家堡子半个多世纪了,当年那些老的少的像电影拷贝一样在脑海里存得好好的。忘不了过去的事的时候,就又像过电影似的一个个闪现在眼前。我们那堡子是穷了点,可人都很勤谨,也很善良的。三娘家的日子好一点,她那笑声村人们就讨厌,嫌她可憎。其实三娘可亲呢,她闲着了就抱住我的头帮我逮虱子。她很少有闲着的时候,只是锥帮纳底时才坐在前门口跟妯娌们聊天。一娘矮矮的个子,很能干。她跪倒麦场里用棒槌打麦,一晌一晌不起来,他们家庄稼颗儿就是她这样捶出来的。她过着艰难的孤儿寡母的生活。远门有个二伯,老是打鸡啼起半夜的,每天赶早出村外顺车渠去拾粪。拾不到粪他也不空手回家,常常是背一捆柴回来。一些家就发现自家的麦秸积少了一豁子。有人就说二伯老是偷偷摸摸的,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手不牢”。可是村上的红白事,家家都请二伯当住事。二伯的人气挺旺。用村人们的话说,这就叫“不记仇”。大家就凭着这,和睦相处,一辈传一辈。
我家属村子里的锡户。六伯名叫锡凯(我父亲的亲哥哥)却是个多事的主。一娘的寡妇娃日子实在无法过前去了,有人给她介绍了个鳏夫。六伯大为恼火,说她败坏门风。六伯有挂挂面的手艺,挺辛苦的。每天下午和面,搓成碗口壮的条,盘进面池里,格一个时辰搓一次条,整整一个晚上的忙活,直到把条搓细,第二天太阳出来上架。那晚他正搓条,有人向他告密,说那鳏夫进了一娘家的门。六伯不问三七二十一,提了根棍扑了进去。人家闻风溜了。六伯的面却饧过了头。他后悔的直骂人家“谎报军情”!
一娘最终实现招赘,给我们村里引入第一个杂姓,那人姓汝。接着经户里也有寡妇招赘,村里又多了个叶姓。两大户族各有杂姓,谁不笑话谁。其实也是世情到那儿了,法律允许寡妇改嫁。也算是我们村里人的一次思想进步吧。六伯后来说,他想起那糊涂事就觉得好笑!
老韩头落脚我们村却大有无缘无故之嫌。他在我们村无亲无故的,因啥别进这个楔子,村里人也不管,说那是人家干部的事。老韩头也没有什么家产,却和大家一样成了农业社的社员。农业社在饲养室旁边的一片空地上给他盖起了房屋,他成了终生饲养员。老韩头脾气不好。饲养室门口有眼井,井台上放着公用的桶和担,谁家挑了水,就及时放回原处。老韩头常为不见了桶担在村头可着嗓子日娘叫老子地骂街,没人嫌这位外来户人给大家撒歪。反倒有人说,村上就得有这样个人讲正义。听说老韩头死的时候已经实行了责任制,各家各户凑钱把他葬进了我们村的公坟里,丧事办得也挺体面。多好的村民啊!
人好,村风就好。村人很骄傲,说咱们村人老几辈没有一个犯律坐牢的。我庆幸自己是这个村里的人!
思念故乡优美散文:游子故乡行
一辆“宝马”牌轿车,沿鄂东蕲河西岸乌黑的柏油公路北上檀林口子镇。车上坐的是应邀参加家乡村级公路庆典仪式的父子俩。
儿子聚精会神地开着车,笑着说:“这比跑沪宁高速还要累得多呢!”
老爸问:“为什么?”
“你看这路上车类混杂,单车道,多岔口,又没有高架桥,”儿子似乎有点委屈,“冤得我'宝马’也不敢提速。”
“不要急,安全第一。”老爸又重复着他的口头禅。他眯着眼望着公路两边徐徐后退的护栏等安全设施和交通警示牌。
“脚踩油门,心想人民”
“不枪一秒锺,幸福一辈子”
“前面有校园,减速缓行”
……
醒目的警示语让老爸感觉到“人本”思想处处得到了体现,社会文明之风已吹进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这位有四十年教龄的中学高级教师,因连续任教高三班主任,长年在外已有十年没有回过老家,他对眼前的一切,感慨万千。唉,过去这是一条什么路呢?当年的民谣还记忆犹新。诸如冰冻一把刀,化冰一团糟;晴天“光灰路”(土话,意为路上尽是灰尘);雨天“水泥路”(幽默话,意为满路都是泥巴和水);老人想起当年往返县城的情境真是终生难忘,人坐车上,颠簸摇晃,过道上,座椅靠背上,司机头上(副驾驶座位和车头空间),都塞满了人和行李包,车厢里拥挤、碰撞、口臭、狐臭,令人窒息,争吵、斗殴时有发生。破车破窗,热天闷死人,冷天吹死人。车祸屡屡发生,在这条路上,许多司机人亡家破,好多乘客残废终身。一个刹车把老人从记忆中拉了回来。车前有个警示牌:“前方施工,行左道”,朝前望去,啊,正在机械铺柏油呢,一节节直线,一根根小线桩,后面是一条条白色清晰的中分线、快行线、斑马线,工人们在上面忙碌着,俨然是五线谱上一个个跳动的音符。铺石机、碎石机、压土机齐鸣,钢板与地面的磨擦声,碎石的撒放声,压土机强烈的筑击声,柴油机排气声,响彻蕲河群山之间,像是在演奏一首农村建设的交响曲。老人想:这声音的美妙之处,只有在外打拼的游子才听得亲,只有热爱生活,乐于吃苦在前的人才听得清,只有勤于思考,勇于奋发的人才听得懂。
小车缓缓而行,密密的路旁树,宽阔的河床,一道道桥梁,清清的河水,沃沃的围田,一片片金黄的稻穗,扑面而来,又匆匆而让;蕲河两岸,群山踊跃,远峰如云似舞,近岭苍黄翠绿,。山下建筑群,鳞次栉比,楼房式样各具特色,有三列两层半的传统中原建筑,有圆顶尖角的欧式建别墅,有飞檐翘角的中国西南梁柱造型,也有脊高檐低黑瓦白墙的海边别墅式样……,它们因山而向,临水而立,楼前有楼,楼上有屋,千姿百态。
儿子情不自禁的说:“老爸,你看,山区都城市化了!”
老爸似乎领悟更深:“我看山乡绿化是城市无可伦比的,香樟漫山遍野都是,大的一棵就有一幢十层楼那么高,没有夸张吧。家家有院,院院都少不了栽种桂花,庭前屋后树种繁多,什么槐树、杨树、柳树、枫树、棕树、皂荚树、桃树、枣树、石榴树、李树、橘树、白杨、梧桐、松柏、广玉兰、木梓、香椿,简直是应有尽有,灌木、花卉就更甭说了。”
“爸,看你又来了,山是故乡美,水是故乡甜,谁不说家乡好呢?”儿子似乎听腻了老爸平素对家乡的颂词。
老爸马上纠正:“不,我们这个地方过去是不行的。”他清楚的记得,三十年前,蕲河两岸,东西两条干渠,绵延百里。农业学大寨,红旗招展,开荒垦田,梯地层层,山欢水笑,但是居民房舍十分简陋,“明三暗五老猪娘,夫妻儿女在一堂,白天老少共一屋,晚上全家睡一床。”老爸熟练地背诵起顺口溜,“大红苕,栎炭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老爸语气沉重的说:“这些顺口溜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家乡人民生活的低标准和低要求。”老爸风趣起来居然绘声绘色地讲起笑话来:说的是那年代,天一亮,一个当家的就喊着儿女们起床干活——“女儿,快把牛牵到你大伯坝头上系着,二毛把牛屎搭到你三婶茅壁上。”儿子摇头笑着说:“那年代也是无奈哟。”老爸也自嘲地笑了一通后,正经起来,然后拖着长腔说:“是的——,那时蕲河两岸几乎找不到一栋楼房,一色的土坯房,下雨倒墙,下雪断梁,屋下百孔(老鼠洞),屋上千窗(泥瓦破洞多)。偶尔有一幢红砖瓦房就了不起了。”
小车开始上山了。说话间他们早已穿过大同、两河口、三角洲、四(细)竹河、已到五子冲,前面就是六里沟,再过七里横排、八里岗,越过九龙潭,方可绕过十(石)玉尖,十(石)玉尖对面有个望八寨,望八寨下有个陈旺村,那就是车上父子俩此行之目的地。远远望去,那密峰丛中的望八寨便是他们老屋后面的顶峰,此时象是在等候着游子的归来。
山区公路虽然弯多且急,坡长而陡,但路面宽均有三米以上,排水沟通畅,低凹处都设有涵洞,小流道道有拱桥,古老的高山庵现已成为移动公司的信号差转站。老教师深知:那矗立的发射塔标志着山区人民已进入信息年代,古庵旁边那段穿崖而过的公路和龙潭拱桥,体现了故乡人建设家乡的坚强决心和聪明才智。
手机铃声打破了车内宁静的空气,原来是村长来电询问他们父子已到达的位置。他们迅速追上前面参加庆典的车队,一会工夫就到达了庆典场地。
鲜花、少年、爆竹、锣鼓把他们拥入庆典场地中央,横幅、垂幅、喇叭、音乐,充满热闹、喜庆的气氛,主席台前,千余名群众摆成方阵。在一阵亲热的乡音爆炒中,父子俩被请上贵宾席,顿时,老人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只晓得鞠躬鼓掌。他的来宾讲话出奇的短,却博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我很高兴的带着儿子回来参加家乡村通公路庆典,仅以一万圆人民币表示我们父子寸心,感谢党中央富民政策,我为父兄们的辛勤劳动给家乡带来巨大变化感到无比自豪,希望家乡明天更美好!”
庆典仪式在小阳春温暖的日光下,完成了既定的程序。但大家仍然沉醉在乡土、乡风、乡气、乡音之中。
午饭餐桌上,父子俩吃到了久违的水煮干花菜,辣椒粉蒸臭豆,滚烫的锅巴粥等本地传统饭菜,还尝到了广东老火力汤、湖南的剁椒鱼头、福建的海仙丸、上海的糖醋排骨、东北的肉炒白菜干豆腐。村长说那精湛的烹调技艺是堂弟在外打工学到的,因为交通便利,乡镇超市什么菜料都能买到的。
一吃完饭,父子俩在叔侄伯儿的簇拥中登高望远,不觉来到望八寨半山腰的火焰山,村长很来劲儿地介绍着,循指而望,陈望水库东边是养鸡场,引进浙江“来杭鸡”,去年养殖一万只,高峰期日产鲜蛋六千枚,年收入三万元,蛋销武汉、黄石等大中城市。西边那边山排上的篱竹,是侄子小强从浙江引进的,近两年仅竹笋一项每年收入就在一万元以上。水库南边畈上种的全是药材,山上到处是木耳培育基地,老二队(七十年代的生产队)成了加工区,过去的生产队保管室被改造成了加工厂,山上那些斗笠丘(面积很小的稻田),都由政府林业部门作退耕还林处理了,还有专业人员守护呢。
离途中,老爸回首望八寨,心潮如诸峰起伏。游子今日匆匆而归,又象当年悄悄地离去;古老的望八寨,在峥嵘岁月,曾有过光荣的历史,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许多神奇的传说。如今看来仍显得巍峨美丽,你披着绿装,撒满阳光,充满生机……
儿子读着老爸那双深邃的眼神,他老人家的意轮似乎挂在一档,碾磨着这美妙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