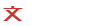巴金散文病中集推荐三篇
巴金老先生他是用自己的思想艺术魅力赢得读者喜爱的。他是用发自内心肺腑的真实感情,与时代共鸣的感情,感染读者的。他用对人类真挚的深沉的爱,去点燃青年读者的心,唤醒他们的良知、人性和爱。下面是读文网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巴金散文病中集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散文病中集推荐二:一封回信
一
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女士最近访问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问题。她这样写道:
我一九七五年来过中国。当时我要求会见作家、访问出版社,不成。我要求给我文学作品阅读,我却为人们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贫乏而感到吃惊……其中叙述了革命,但并没有文学,或者至少没有我们西方人所谓的“文学”。
现在,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变化?形式在中国是不是也变得重要起来了?您是怎样看待这个变化的?您说过:“要相信未来。未来将是美好的。”您怎样看这未来呢?中国目前出现的西方化的倾向太显著,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苗头,您以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鸣放期间我写过文章,劝人运用独立思考。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我又否定了自己。后来吹起了一阵暖风,我的思想稍微活动起来,于是““””发生,我被打翻在地,还有一只脚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动弹不得。“_”垮台以后,我又站了起来,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了。对每件事我都有个人的看法,对有的问题我考虑得多一些,有的考虑得少一些,不过总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虑。我常常想,最好等考虑成熟了再开口讲话,但实际上我常常被逼着发表不成熟的意见。我想既然给逼上梁山,那就说吧,横竖是说自己的话,说错了就认错,受到责难,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书桌上乱纸堆中睡了十多天,终于给找了出来。无法避开她的问题,我写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动不便,没有能接待您,请原谅。您要我‘用书面回答’您的问题,我写字困难,只能简单地写一点;而且,当然,只讲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话时,我也并不代表别人。
“一九七五年在‘_’专政下,我还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分子’,一个‘新社会’的‘贱民’,我早已被赶出了文艺界,您当然不会见到我。您也不会见到别的写过文学作品的作家,因为他们全给赶到‘五·七’干校或者别的地方劳动去了。‘_’用极左的‘革命’理论、群众斗争和残酷刑罚推行了种种歪理:知识罪恶,文化反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加速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害怕反映真实生活的文艺,他们迫害讲真话的作家。他们开办‘工厂’,用自己发明的‘三突出’、‘三结合’等等‘机器’制造大批‘文艺作品’,他们得意地吹嘘‘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结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们制造的‘作品’都是他们用来进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在那一段时期出现的‘作品’里,既没有生活,也没有革命,更没有文学。有的只是谎言。不到十年,它们全给扔进了垃圾箱。
“现在的确有了像您所说的那种根本的变化。‘_’垮台了,他们的‘阴谋文艺’破产了。作家们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拿起了笔,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在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们也给恢复了名誉,重新得到执笔的权利和自由。大家都在勤奋地写作。几年来出现了相当多的文艺刊物,相当多的新作家,不用说,还有读不完的各种各样的新作品。作品很多,当然有好有坏,但好的并不少,我只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却保留着很深的印象:这里有生活,有革命,也有文学;而且还有作家们的辛勤劳动和独立思考。作家们各有各的风格,各人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了解的人物,生活多种多样,人物也有不同的光彩。在这些作品中我看到我日常接触的平凡人物,我发现我的同胞们的优美心灵。我很高兴,我看到了百花初放的景象。这不过是一个开始,我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我说‘前程似锦’(‘未来将是美好的’),我是有理由的。那许多经过十年‘“”’的磨炼,能够用独立思考、愿意忠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更深刻的作品。当然也会有不少的阻力。但是大多数作家写作,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是想改善周围的生活,使生活变得美好,使自己变得对社会、对人民更有用。现实生活培养了作家,它像一根鞭子逼着作家写作、前进。认真的作家是阻力所难不倒的。
“用不着担心形式的问题。我个人始终认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写作的道路上中国作家从未停止探索,总想找到一种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自己思想、使它打动人心的形式,就像战士们总想找到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让他们自己挑选吧。读者们的锐利的眼光正在注视他们。
“至于西方化的问题,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我们在谈论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我还看不出什么‘西方化’的危机。拿我本人为例,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但我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始终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旧作,我并不觉得我用的那种形式跟我所写的内容不协调,不适应。我的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它们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没有采用我们祖先用惯了的旧形式。我正是为了反对旧社会制度,有志改善旧生活、改变旧形式,才拿笔写作的。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现手法,他们有创新的权利。他们或成功或失败,读者是最好的评论员。作家因为创新而遭受长期迫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成为社会的东西,好的流传后世,不好的自行消亡。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现在不再是‘_’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时代了。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因此我不在信里谈克服所谓‘西方化倾向’的问题了。”#p#副标题#e#
巴金散文病中集推荐一:一篇序文
一
我知道魏以达同志把我的《家》译成了世界语后十分高兴。三十年代中我曾经想望我的长篇小说有一个世界语译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动手试一下。那个时候我经常接触世界语书刊,使用世界语的机会较多。可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够严格,下不了决心,害怕开了头完成不了,一天拖一天,后来别的事情多起来,我和世界语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世界语又由熟悉变为生疏,也不能再做翻译自己作品的考虑了。
四十几年过去了。中间我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十载““””,但是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却始终不减。我为近四十多年来世界语运动的发展感到兴奋。我个人的心愿也并不曾落空,我想做而没有能做的事情魏以达同志替我做了,而且做得好。他不是按照英文删节本翻译,他根据的是我在一九五七年改订过的中文原本(一九七七年版)。我希望什么时候也出现一个完全的英译本!我不喜欢整章的删节。
《家》不是自传体的小说,不过我在书中写了一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像高家那样的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在中国似乎已经绝迹,但封建社会的流毒还像污泥浊水积在我们的院内墙角,需要我们进行不懈的努力和不屈的斗争,才能把它们扫除干净。有一个时期连我自己也误认为我的小说早已“过时”,可是今天我还感觉到我和封建家庭的斩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可怕了!我才明白我的小说并没有“过时”。
当然它总有一天要“过时”,我是指到了污水给打扫干净的时候。但新社会总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要了解今天的人,就不能忘记昨天的事,我们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对我来说,《家》今天还是警钟,多么响亮的警钟!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
以上是《家》的世界语译本的序文。在翻译这小说的时候,译者曾来信要我为译本写篇短序,我说我为《家》的重印本和一些外文译本一共写了十篇以上的序,说来说去,意思相差不多,我不想再炒冷饭,决定不写什么了。后来见到译者,我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出版社准备发稿,来信中又谈起了写序的事,我一口答应,动笔写了六七百字,过两天就寄出去了。
惟一的原因是:我有话要讲。但在序文里我只是简单地讲了几句,我害怕读者会感到厌烦。我读小说就不看什么前言、后记,特别不喜欢那些长篇大论。
在短短的序文里我讲了两件事情:一,我对世界语仍然有感情;二,我不喜欢删节过的英译本《家》。
先谈世界语,一九二一年我在成都的《半月》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世界语之特点》。当时我不到十七岁,还没有开始认真学习世界语,我只是在这之前在上海出版的什么杂志上读过宣传世界语的文章,自己很感兴趣,就半抄半写,成了这篇短文。短文发表以后,有一位在高级师范念书的朝鲜学生拿着《半月》来找我商谈开办世界语讲习班的事。我只好告诉他,我写文章是为了宣传,我手边连一册课本也没有。他也懂得不多。因此讲习班终于没有办起来。
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念书,找到了世界语课本,便开始学习,每天一小时,从不间断。读完课本,我又寄钱到上海一家很小的“世界语书店”,函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仍然每天一小时(或者多一些),遇到生字我就求字典帮助(我有一本英国爱丁堡出版的世界语 —英语小字典),一个字也不放过。一本书读完,我又读第二本。那家惟一的世界语书店里只有寥寥的几十种书,不过也能满足我的需要。它有什么书,我就买什么书。首先我读了一本厚厚的《基本文选》,这是创始人柴门霍甫编译的。接着我又读了《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和别的一些书,如卜利瓦特的《柴门霍甫传》等等,不到一年我就可以自由使用世界语了,在通信、写文章这方面用得多些。到一九二九年我才开始用世界语翻译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也不过薄薄的四五本,其中有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用世界语写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此外,我还为上海世界语学会编辑了几期《绿光》杂志,在上面发表了两三篇像《世界语文学论》那样的文章,谈个人的印象,当然很不全面,因为我读书有限,只读了学会的半个书橱的藏书,而且不久连这些书也被“一·二八”侵沪日军的炮火毁得干干净净。这个学会在闸北的会所给烧光之后另在“法租界”租了一间屋子,继续活动了一些时候,到一九三三年就“自行消亡”了。
以后成立了新的世界语学会,但是我已经离开了运动。我是旧学会的会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从法国回来不久参加了学会,后来又当选为理事。在““””期间“巴金专案组”的人审讯我的时候,就揪住这个“理事”,这个“会员”不肯放。他们问来问去,调查来调查去,我在解放前就只参加过两个团体,另一个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我也是这个协会的理事,别的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他们梦想发现什么“反动集团”,结果毫无收获,幸而他们只会使用斥骂、侮辱这一类的手段,没有采用严刑拷打(文艺界中吃过这样苦头的人确实不少),否则我也不可能在这里漫谈对世界语的感情了。这感情今天还存在。虽然我已经没有精力继续做从前做过的那些工作,但是我仍然关心世界语的事业,并且愿意为它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再过五年,一九八七年,将是世界语诞生的一百周年。一百年!它应当有更大的发展。
三
关于《家》,几十年中间我讲了不少,现在似乎无话可说,其实也用不着我饶舌了。
这次我在序文里提到英译本中整章的删节,并且表了态,只是因为编辑同志来信说:“我们发现英文版有较大的删改,据说是你亲自为外文版删改的。”他们“征求”我的意见:世界语版的内容以中文原本为根据,还是按照删改过的英文版。
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表态了。其实我早就应该讲话。从一开始我就不满意那样的删改法。但删改全由我自己动笔,当时我只是根据别人的意见,完全丢开了自己的思考。这“别人”便是中文底本的责任编辑,由他同我联系,底本大概也由他定稿。他的理由似乎是:一切为了宣传,凡是不利于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等等。他的意见我全部接受。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此外,我还有一张护身符:“政治标准第一”嘛。我在“双百”方针发表前交出了删改本,英译本则在反右运动后出版,我害怕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作家,不爱护自己的作品,却拿它来猎取名利,这也是一件可耻的事。英译本可以说是照出我的“尊容”的一面镜子。让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吧。
现在,我的座右铭是:
尽可能多说真话;
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p#副标题#e#
巴金散文病中集推荐二:病中(3)
整整七个月我不曾在书桌前坐过片刻。跟读者久别,我感到寂寞。我是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里摔断左腿给送进医院的。在好心的医生安排的“牵引架”上两个月的生活中,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噩梦的折磨,也不断地给陪伴我的亲属们增添麻烦和担心(我的女儿、女婿、儿子、侄女,还有几个年轻的亲戚,他们轮流照顾我,经常被我吵得整夜不能合眼)。我常常讲梦话,把梦景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听见我在床上自言自语:“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有时头脑清醒,特别是在不眠的长夜里,我反复要自己回答一个问题:我的结局是不是就在这里?我忍受不了肯定的回答,我欠下那么多的债,决不能这样撒手而去!一问一答,日子就这样地捱过去了,情况似乎在逐渐好转,“牵引”终于撤销;我也下床开始学习走路。半年过去了。
我离开了医院。但离所谓“康复”还差很大一段路。我甚至把噩梦也带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发出怪叫,或者严肃地讲几句胡话,种种后遗症迫害着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静。白天我的情绪不好。食欲不振,人也瘦多了。我继续在锻炼,没有计划,也没有信心。前些天我非常害怕黑夜,害怕睡眠,夜晚躺在床上,脑子好像一直受到一个怪物的折磨。家人替我担心,我也不能不怀疑:“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来?”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坚持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我不相信噩梦就能将我完全制伏。这两夜我睡得好些,没有梦,也没有干扰。女婿在我的床前放了一架负离子发生器,不知道是不是它起了作用。总之睡眠不再使我感到恐惧了。
在病中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写信的有不少熟人,也有从未见过面的读者。除了鼓励、慰问的话外,还有治病经验、家传秘方、珍贵药物,等等,等等。最初将近三个月我仰卧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听孩子们给我念来信的内容。那么真挚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的流了眼泪。我无法回信,而且在噩梦不断折磨下也记不住那些充满善意的字句。信不断地来,在病床前抽屉里放了一阵又给孩子们拿走了。我也忘记了信和写信的人。但朋友们(包括读者)寄出的信并未石沉大海,它们给了一个病人以求生的勇气。倘使没有它们,也许今天我还离开不了医院。
我出院,《大公报》上发表了消息,日本朋友也写信来祝贺。我在医院里确实受到了优待,在病房内几次接待外宾,还出院去会见法国总统。《寒夜》摄制组的成员到过病房,找我谈塑造人物的经过和自己今天的看法。还有人来病榻前给我塑像,为我摄影。最使我感动的是春节期间少年宫的儿童歌舞团到医院慰问病人,一部分小演员到病房为“巴金爷爷”表演歌舞。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我耳边报告节目,并做一些解释,他们表演得十分认真。看见他们告辞出去,我流了眼泪。
我在医院里度过春节。除夕的午后女儿告诉我,孩子们要带菜来同我一起吃“团年饭”。我起初不同意,我认为自己种的苦果应该自己吃,而且我已经习惯了医院的生活。但是孩子们下了决心,都赶来了。大家围着一张小桌匆匆地吃了一顿饭,并没有欢乐的气氛,我也吃得很少,但心里却充满了感激之情。刚吃完这一顿“团年饭”,孩子们收拾碗筷准备回家去(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妇来了。他们说过要陪我度过除夕,还约了罗荪夫妇。孩子们走了,他们一直坐到八点,他们住在静安宾馆,来往方便。我这种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动了他们的心,曹禺又是一向关心我的老友,这次来上海,几乎每天都要来探病,他比较喜欢热闹,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给我。我和我兄弟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他们夫妇穿上大衣离开病房。
我兄弟照顾我睡下不久,罗荪夫妇来了,他们事情多,来迟了些,说是要同我一起“守岁”,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进入半睡眠的状态,他们同我兄弟谈了一会,也就扫兴地告辞走了。
我想,现在可以酣畅地睡一大觉了。谁知道一晚上我就没有闭过眼睛。友情一直在搅动我的心。过去我说过靠友情生活。我最高兴同熟人长谈,沏一壶茶或者开一瓶啤酒,可以谈个通宵。可是在病房里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讲几句,多坐一会,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难道你变了?”我答不出来,满身都是汗。
“把从前的我找回来。”我忽然讲出了这样一句话。不仅是在除夕,在整个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一句。但是连我也明白从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来的了。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十年““””决不是一场噩梦,我的身上还留着它的恶果。今天它还在蚕蚀我的血肉。我无时无刻不在跟它战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发现,在我儿女、在我侄女的身上还保留着从农村带回来的难治好的“硬伤”。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梦话。即使我的结局已经到来,这也不是“一个悲剧”。即使忘掉了过去的朋友,我想我也会得到原谅,只要我没有浪费自己最后的一点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草地边有一个水池。这次我住在三楼。八○年七月我在二楼住过,经常倚着栏杆,眺望园景,早晨总看见一个熟人在池边徘徊,那就是赵丹,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个月后就要跟这个生龙活虎般的人永别。三年过去了。这次住院,我行动不便,但偶然也在栏前站立一会。我又看见水池,池边也有人来往,也有人小坐。看见穿白衣的病人,我仿佛又见到了赵丹,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他那响亮的声音呢?!
我在栏前看见过黄佐临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这位有名的戏剧导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里,春节大清早,他进来给我“拜节”。同来的还有影片《家》的编导陈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进房。他是二楼的老病人,身体差,谈得不多,但熟人见面,有说有笑。几个月过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楼去看过西禾两次:第一次他在睡觉;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连连说:“非人生活。”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想起四十年代我们在霞飞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剧本《沉渊》的演出,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剧《这不过是春天》中有声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泪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话都吞在肚里,我多么希望他活下去。没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讣告。什么话都成了多余,他再也听不见了。
巴金散文相关